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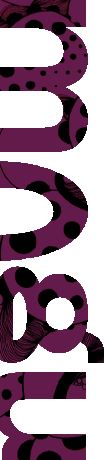
| 富邦藝術小餐車17-「MoguMogu」策展理念 | 策展人/張元茜 |
|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天是豐收的季節,生命在此時呈現其豐美的成果。秋天雖忙碌,但卻也是眉開眼笑的。農人至此總算解除了「易種難收」的焦慮,而播種者與收成物之間盈盈相望的一刻,實現了物我兩相融的境界。秋,有著收成所釀造的繁華,也有一年辛勤後答案揭曉的坦然與安心;有著對時間流逝摧折之慨,卻也有來年再生生不息的期盼。 在這個季節裡,富邦藝術基金會將以Mogu Mogu一展,為公共空間注入豐收的氣氛。「Mogu」這個音是來自蘑菇,蘑菇是一種農收物,它是菌類植物,以孢子繁衍,是屬於地球上最古老的一種繁衍及生長的方法,一直到現在,孢子繁衍的生命力仍然強健,尤其在台灣這樣的亞熱帶環境中,菌類植物繁茂豐盛。蘑菇狀如傘蓋,是童話故事中最好的遮陽避雨處,也是桌上佳餚,甚至是魔幻食材的代名詞。「Mogu」另一意思「磨姑」,在中文意指緩慢的步調,是一種思索的過程,強調游移、慎思、斟酌;在日文中媽媽總是要孩子在吃飯時多「mogu mogu」,意思是多細嚼慢嚥,仔細咀嚼,不要囫圇吞棗。這種放慢腳步、慎思而行的價值正可以解決物質文明的競爭,甚至於人性走樣的焦躁。每天打開電視新聞,充斥著我們被狂風暴雨、政治事件、戰爭、病菌、意外災禍、不潔環境所威脅的不安,那麼「磨姑」的精神或許是對抗這種不安的一帖良方。在游移、慎思及斟酌中,可以湧現智慧;放棄了對速度的一昧追求,可以得到事緩則圓的回報。 秋水季節富邦藝術基金會推出「Mogu Mogu」一展,一方面對秋水禮讚,另一方面也希望以這個展覽與觀眾分享莊子秋水篇中一些河伯式的對話。莊子秋水篇的主角叫河伯,掌管百川,在秋水漲滿之際他意氣風發,欣然自喜。但是當他順流而下來到北海,才知海比他想像的大許多,讓他望洋興嘆,並與北海海神展開一連串精采的對話,由河伯提問,海神為他解釋如何去除成見,以免妄下斷語,並達到虛懷若谷,物我合一之境。秋水成為莊子最膾炙人口的經典篇章。「Mogu Mogu」也希望以展覽方式成為現代河伯式對話的引子,例如我們邀請藝術家許唐瑋以及麻粒試驗所設計一個巨大蘑菇,站立在敦化南路上富邦人壽大樓的廣場,原本長在角落的蘑菇,在展現非凡尺度後,讓我們看到蘑菇風華的紋理及圖案。 好奇如河伯者,必然會問:「蘑菇明明這麼小,為什麼會做這麼大的蘑菇?」北海神的回答應該是「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你怎知道毫末就是最細微的極致,而天地就是無盡的最大範圍呢?)展覽中的藝術家以巨大的蘑菇反寫生命的尺度及進化的倫理順序,實踐北海神所謂「物無貴賤?的胸襟,同時也以普普或KITSCH主張玩物,卻也敬物的意味完成這件行動公共藝術作品。這件由於設計時已詳細規劃這種無地基的大蘑菇將四處游走,因此菇體內裝有水槽,放置在廣場後灌水,壓低重心,移動時則放水減重。如此身段靈活,走動自如,加入富邦藝術基金會這兩年來已製作出的其他幾件移動式公共藝術作品(一杯子的祝福、帶祿獸)的行列,將四處「 除此之外,我們也邀請寶大協力、潘娉玉等藝術家製作較小型的蘑菇,以各種材質描繪群聚蘑菇的千姿百態。當藝術家解開材質的限制,勇敢啟用現成物及工業產品時,我們開始真正感受到金、木、水、火、土之外的混搭材質,這種質感已充斥在生活中,卻一直等到藝術家精準的用在臆想不到的造型上,我們腦中真正開始顛覆了材質在貴賤、粗細、有用、無用上之成見,同理,圖案之大用亦如是,像許唐瑋、洪意晴的蔓延繁衍的圖案形成空間的層次感及迷離效果,顛覆內外表裡之分,只有不斷蔓延的纏綿糾結圖案。許唐偉在大磨菇上畫滿了類似小機器或小玩具,甚至是細胞微生物的紋理,遠看也像菌種圖案,化約了無機管線與有機生命的界線。 我們也邀請林銓居的稻米計畫參展,這個計畫是藝術家本人親身參與割稻、打榖、推草、焚草的過程,生以肉身體驗父親輩農人對收成的心情,以及對生命循環後又生生不息的期待。藉此向父親靠攏,與大地接近,也重溫千古以來人與作物之間的親密關係。 豐收的季節裡,富邦藝術基金會也完成這一季的豐收,我們希望未來將這些行動公共藝術作品帶到台灣各個角落,像飄散的孢子般,將想像及創意的種子四處繁衍,每到一處展覽一段時間後,作品就再度移動,所以我們不對空間佔有,相反的是以時間換取空間。作品在各地展出多年後或許斑駁、或許脫落,但是對每一個曾經駐留之地的觀者而言,對作品的回憶,會形成視覺的詩篇,像秋水篇般不斷傳頌。 |
|
